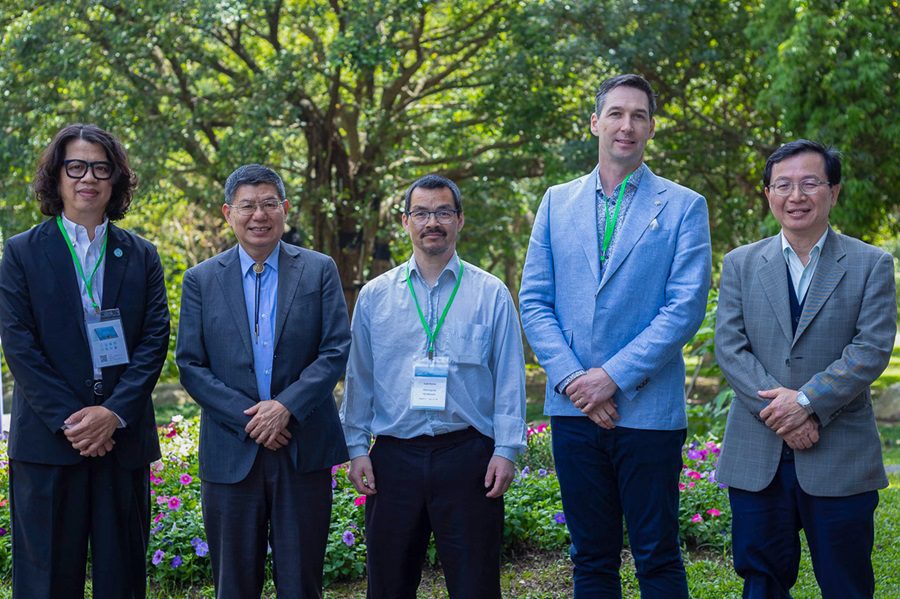
記者翁一如/綜合報導
2025年4月14日,來自格陵蘭的寒意吹進台灣,卻在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化為一股深切的思辨暖流。首場《IPCC國際論壇:北極的最後一塊冰》隆重揭幕,來自極地冰原的氣候科學家、因紐特獵人與近300大學生、學者、媒體線上線下共聚一堂,展開一場跨越學術、文化與世代的深度對話。
這不只是一場氣候科學的論壇,而是一段關於未來的敘事——從冰川崩裂的聲音、雪橇犬無法歸家的無奈,到企業決策者面對冰原時的省思與轉變,每個人都在這場對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責任與行動起點。
 ▲「IPCC國際論壇」大合照。(圖/歐萊德提供)
▲「IPCC國際論壇」大合照。(圖/歐萊德提供)
若無作為,海平面將上升達 2 公尺
首位講者威廉博士(Dr. William Colgan),來自丹麥與格陵蘭地質調查局,是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(IPCC)AR6報告的核心貢獻者之一。他長年於格陵蘭冰蓋實地研究,提出著名的「僵屍冰」(zombie ice)理論,用來形容那些已註定融化、無法挽回的冰塊。
威廉以ㄧ張投影地圖,指出台北與格陵蘭伊盧利薩特之間的距離——9,300 公里。「看似遙遠,但當海平面上升82公分,這段距離將在洪水中瞬間消失。」
威廉指出,即便全球立即停止碳排放,格陵蘭仍有約3%的冰體會融化,造成27公分的海平面上升,這是不可逆的;但若我們什麼都不做,本世紀末海平面可能上升至2公尺,台灣沿海與河口城市將首當其衝。
威廉特別強調:「海平面上升,不只是洪水或倒灌,更會滲入城市的淡水系統,污染飲水、破壞農業與基礎建設,造成長遠而無法挽回的損失。」
威廉語重心長地說:「科學能做的是建立模型與預測,但真正的轉變,來自由下而上的行動,包括消費者、政策制定者、市民的每一個選擇與連結。」
「很多人覺得台灣與格陵蘭無關,但如果你家住在海邊,那麼格陵蘭就在你身邊。」
 ▲「IPCC國際論壇」共同呼籲:再不行動,海平面恐升兩公尺。(圖/歐萊德提供)
▲「IPCC國際論壇」共同呼籲:再不行動,海平面恐升兩公尺。(圖/歐萊德提供)
「我不知道怎麼回家了」——當北極獵人面對融冰無路可返
站上舞台的第二位講者,是來自格陵蘭北部 Savissivik 聚落的因紐特獵人奧倫瓜克・克里斯坦森 (Olennguaq Kristensen),擁有七個孩子、五個孫子、45頭雪橇犬的他,同時也是當地獵人協會主席。他從13歲起踏上冰原,如今年近半百,卻目睹祖先世代所倚賴的冰層正逐年消失。
奧倫這次來台,橫跨16,400公里,歷時兩週才抵達。論壇開始前,他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:「你回家的那條路,本來七月才會融冰,現在卻開始融化。」
同樣關注氣候邊謙的國際論壇主持人路怡珍在現場向奧倫提問:「氣候變遷對你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?」
奧倫看著滿場觀眾,語氣平靜的說:「地形變了,冰層不再堅固,雪橇犬無法承重,我們能打獵的地方變少了。我來這裡的時候,還能走回家。但現在,我不知道該怎麼回家。」
奧倫話音剛落,全場一片沉默。這不只是環境問題,而是一段文化與家園逐漸流失的真實情境。
每一個人,都是氣候拼圖的一塊
《解凍格陵蘭》團長暨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分享了他站上冰原時內心的動盪——看見冰層崩塌的那一刻,他不只是震撼,而是下定決心。「我不想只是拍照、打卡、感動,我想改變。」
扎根環境教育、把國際資源帶進來,是四次前進聯合國的葛望平董事長心願。就在論壇前一日,他親自陪同奧倫首次造訪大安森林公園——這是奧倫人生中第一次離開格陵蘭、第一次出國、第一次走進台北。他伸出手觸碰人生遇見的第ㄧ棵樹。對我們來說再平常不過的日常,對他而言,是全新的世界。
「一個人的行動固然重要,但當我們一起做,一切就會不一樣。」葛望平說。
這個思維也呼應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詹長權院長於致詞時所言:「格陵蘭是我們的未來鏡子,理解它,就是學會面對未來。減碳不一定要從工廠開始,它也可以從我們的飲食、交通、消費做起。」
改變,從格陵蘭的眼睛看世界
這場論壇不只是遠方的北極之旅,更是一面面對現實的鏡子。當主持人路怡珍再次問奧倫:「你希望我們做些什麼?」
奧倫沒有用數據,也沒有提出倡議,只靜靜地回答:「我們的家還在,但需要有人願意看見。」
看見,就是改變的開始。
接下來,《IPCC國際論壇》系列將持續前進:4月15日台北場將深入討論企業的因應與調適、4月16日高雄場則聚焦城市與企業的創新行動。
地球不會等我們準備好才發出警訊。而今天,來自北極的聲音,已在台灣響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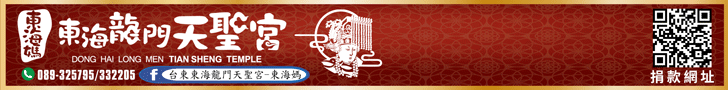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公民幫推協會理事長黃建興、前馬來西亞檳州行政議員鄧章耀、清福醫院院長王炯琅、中華生技醫藥行業協會理事長陳建州藥師-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